
- 公示公告
- 站内检索
- 便民服务
- 在线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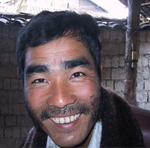
寻找最具有代表性的阿昌族家庭,当然要寻找一户对名扬天下的户撒刀有着深刻理解与权威诠释的家庭,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或者说,这种困难的存在是因为每个家庭都有可以代表阿昌族的理由。打个比方,当某条流水线的100道工序都摆在你的面前时,你能确定谁能代表这条流水线而谁又不能吗?
当我们以“户撒刀”来为一种商品命名时,我们发现,其实“户撒刀”是非常支离破碎的:在它的产地,几乎每一个寨子都“寸有所长”,每一个寨子都“尺有所短”——打制菜刀、土刀、镰刀、砍柴刀等农用刀具要到上芒东,下芒东打的是马刀和宝剑,来细和芒海只打兵刀、匕首等短刀,做刀鞘要到下户昔和芒派,甚至刀把和刀带也分别由两个寨子加工。
而在风俗方面,他们统一每年有两次重要的赶摆:正月初六,皇阁寺赶摆(阿昌族的赶摆起源于道教,却在寺里举行,也算是宗教精神的“兼收并蓄”罢);十月十二,赶塔摆(为庆祝一年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一项活动)。他们吃糯米粑粑和过手米线(非过桥米线。将米线放在掌心,加调料后食用),小伙子们已经习惯了穿着西服结婚——这些,他们都一样。
我们走进户早村的芒海寨子时,户早村党支部书记雷顺广说,因为附近有好几户人家娶儿媳、嫁女儿,几乎整个寨子的户主都去吃酒了,所以这时候很少有人打刀。正说着,一阵“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传了过来。循声找去,在一个简易的工棚里,寸财广正带着他的徒弟、也是他的亲侄儿寸忠跃锤打着长的兵刀,他唯一的儿子寸爱三则熟练地调整着火炉里兵刀毛坯的加热部位,同时还要负责把锤打完毕的兵刀淬火。
他家是户早村打刀历史最悠久的。于是我们走近了寸财广和他的父亲寸老四、母亲康拉来。
“手艺人是饿不死的”
寸老四已经老了。虽然只有67岁,他走路的姿势已经完全是一个老人的姿势,速度很慢,眼睛也有些混浊了,当他颤颤巍巍地蹲下身子去拿东西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的腰部能否承受住他身体的重量。
所以,当他告诉我就在一年之前,他还到瑞丽去帮着三儿打制户撒阿昌刀的时候,我睁大了眼睛。像寨子里的很多人一样,寸老四也把自己的生命和名扬天下的户撒刀紧紧地熔在了一起;当他远离了飞溅的火星、铿锵的锤响,他就像失去了水源的楼兰古城一样迅速衰败。
寸老四是这个打刀世家的第二代,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父亲本来家贫,又有了寸老四等4个儿子,生活一直非常窘迫。来细寨子一位姓康的朋友非常同情他,就让他去给自己帮忙。父亲就这样,一边打工,一边学会了打刀的整套技术,然后就回家自己开铺打刀。就这样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
1948年,因为国内战争频仍,物价飞涨,生活日益困难,父亲只好带着儿子们到了缅甸北部重镇腊秀。作为紧缺的手艺人,他们大受欢迎。寸老四记得有一次,腊秀的水傣(傣族的一个支系)起兵反抗缅政府,他们特意派人到他们的刀铺里传话说:不久这里将要发生战斗,你们最好歇业一段时间,隐蔽一下,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寸老四说,其实他们是怕我们打的刀落入政府军的手里,但他们又不想得罪我们,只好用这种比较委婉的方式让他们避开。
1950年春节前夕,缅甸的局势进一步紧张,人命如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随时会被抓走当兵或者出苦力,稍有不从,就会被关入地牢甚至枪毙,父亲就带着孩子们回到中国。不久,寸老四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兵,参与了对当地土司的斗争。至今,他还记得自己抓捕和看守土司的“警卫队”的情形。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打刀的手艺,寸老四一家过得也不很困难。早在1963年,他和二哥就被合作社定为专门打刀的6个师傅中的两人——这6人集中在一起工作,主要打制一些农用工具,如带锯齿的镰刀等。每天不管工作多少,他们都可以获得一个成人一天的劳动价值:12个工分。
然而,寸老四还没来得及衰老,世事又有了变化: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信息流通加快,有了横向的比较,仿佛是从梦中突然醒来,寸老四和他的儿子们发现原来更美好的生活还在前面,通向幸福彼岸的手段就是——打刀。
因为曾经到过国外,寸老四知道傣族村寨一般较为富裕,而且基本没有打刀的人,户撒却因打刀的农户太多,价格上不去,就决定走出户撒去打刀。由于当时大儿子寸老翁和二儿子寸老常(阿昌族人对姓名看得很淡,所以不讲行辈、父子姓名相似乃至相同的所在多有)成家已久,生活安定,不愿远行,他就先后带着三儿寸长财和四儿寸广财到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瑞丽等县(后均改为县级市)。寸老四慢慢地在这些地方都扎下了根。后来,随着衰老程度的加重,他慢慢地把外边的业务都交给了长时间跟他跑外的三儿子寸长财。
除了老三寸长财和老四寸广财,寸老四的其他3个儿子也都以打刀为生。每一个儿子,都是他手把手地教出来的。寸老四说,从当徒弟抡大锤到当师傅敲小锤,大约需要五六年的时间。儿子们真正独立操作的标志是结婚一年后的分家。那一天,寸老四给儿子置好打刀的一套家什,搭好工棚,就完成了自己对这个儿子的所有义务。
虽然寸老四不说,但他确确实实有着“技术至上”的思想。他的说法是:“手艺人是饿不死的,不管什么样的时代。”
“阿昌不带刀”
从寸老四到寸财广,再到第4代的寸忠跃和寸爱三,都很沉闷,他们对来访的客人保持着足够的客套,这种客套甚至变成了拘谨,让人很难相信,他们就是在现代社会中,用原始的铁锤和人力打制冷兵器的血性汉子。
事实上,除去商业原因,在阿昌族人的生活中,自己亲手打制的户撒刀,远远不如它在与阿昌族相邻的其他一些民族的生活中更重要。在景颇族中,每个青年男子都至少拥有两把刀:“景颇长刀”用于到山上割草、砍柴,另一把短一些的则用于对偷袭者的防范——刀身太长,会限制拔刀的速度。青年男女结婚时,岳父送给女婿的最不可缺少的礼物,就是一把锋利的长刀。据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赶街”时,还能经常遇到身背两把甚至更多户撒刀的年轻人。而现在,作为人们跳舞时的一个摆设,已经逐渐成为户撒刀在景颇族里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缅甸人同样喜欢户撒刀。比如我们采访过的“克钦邦”反政府武装,他们几乎人均两把,也是一短一长,不同的是,由于枪支弹药老旧而且稀少,所以长刀成为他们作战的武器之一,而短刀用于在原始森林中穿行时开路。寸财广告诉我们,他打的刀多半都流入了缅甸,因为他的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锋利,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中国人已经很少要求刀具的实用性能,比中国落后一些的缅甸却正好用得着。我们注意到,寸财广打“兵刀”时用的材料是从废弃的eq140货车上拆下的钢板弹簧,其锋利与耐磨性不问可知。
后来到临沧地区的沧源佤族自治县采访佤族家庭时,我们吃惊地发现,那里的刀具也来自户撒。佤族是一个充满了野性之美的民族,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还有“砍人头祭谷神”的习俗,各寨之间相互以猎取到对方的人头为自豪,刀锋锐利而使用方便的户撒刀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但他们自己却从来不会打刀。
当然,阿昌族也不是完全不用户撒刀。像云南省其他的少数民族一样,阿昌族也是烧火塘的,每天,在寸财广和徒弟升火打刀的时候,妻子就提着长刀上山砍柴。几乎每一个阿昌族庭院里,都有一垛又长又高的柴垛,而没有木柴存储的家庭会被族人瞧不起的。
户撒乡水利站的穆有洪告诉我们,长刀在阿昌族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进新房”:结婚那天,新娘在后面拉着新郎衣服的下摆往前走,新郎一手提刀一手提着一只“童子鸡”;走上新房前的台阶时,新郎就用刀背在鸡的脖子上象征性地一抹,然后就把鸡丢开,宾客、亲友们谁抓住就归谁;走进新房,新郎把一包首饰献给新娘,然后把刀塞在枕头下面,以此来祈求两人今后生活的幸福安康;结完婚,那把长刀就可以随便用了,砍柴、割草都行,但绝对不能卖给别人——不管家里的经济出现了怎样的困难。所以,如果你能在阿昌族家庭里搞到一把家庭主人“进新房”时用的长刀,那你肯定不是花钱买来的,但却一定进行了极大的感情投资——以心换心,憨厚、淳朴的阿昌族人把你当成了自家人,才会把凝聚着自己年轻时的憧憬和渴望的长刀“送”给你。
成也锋利 衰也锋利
手艺人是饿不死的,但饿不死并不意味着吃得饱,更不意味着脱离生存的威胁、进入享受生活的境地。
作为户早村打刀历史最长的寸家,寸老四的二儿寸老常却在2001年初转行搞房屋建造。由于本地建房用的都是木头,从砍伐到加工再到建造,过程相当繁琐,他不得不请了两个帮手。他说,一个月可以完成两间房屋,除去两个帮手每人500元的工钱,他自己可以拿到800元。他说,虽然这种活不是经常有,但无论如何也比原来打刀强。寸广财说,现在他打一天刀大约可以赚到10来块钱,考虑到一年只能有200来天的农闲,一家人从赫赫有名的户撒刀上获得的收入很有限。寸财广也曾经像三哥寸长财一样,到大理、瑞丽等地去打刀,但结果并不理想:外边的电费、木碳都贵得多,而且一大部分要赊销,零售商要把刀卖掉以后才给他钱,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死账,“抛家舍业的,划不来”。
离开户撒乡的时候,我们买了几把刀。但到了陇川县城,旅游局的杨杏局长却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想把刀带回去,就必须在陇川县装入木盒邮寄回去,否则,出了陇川,遇到武警的边防检查,就会被当作“凶器”没收掉。这让我们想起寸财广所说的:在瑞丽和西双版纳等地,如果把户撒刀——此处特指长刀、马刀、匕首等杀伤力较强的刀具——摆在柜台上出卖,也经常会被工商部门查收。同样的感慨来自一位北京的法国留学生。他在户撒住了一个多月,他说,如果户撒刀出现在法国,一把卖上三五百甚至上千元并不是什么难事,问题是它不能合法地出境。
穆有洪说:“户撒刀,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说这话的背景是:户撒刀曾经畅通无阻的中国刀具市场,现在已经成了浙江和四川刀具生产商的天下,长此以往,户撒刀极有可能从市场上消失。户撒乡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努力想成立一个有限公司,统一负责户撒刀的生产与销售。但因为户撒刀背着“凶器”的名声,该公司一直得不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直到现在,户撒刀都没有成规模生产与销售公司。
而在10几年前,状况不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可以称得上是户撒刀的“黄金时代”。寸财广说,现在每片2.5元的兵刀刀片,那时可以卖到3.5元左右,他每天可以赚30多元。那时候,云南、甘肃、西藏、新疆等省就像一个专门消化户撒刀的无底洞,户撒人唯一的忧愁,是如何加工更多的刀以满足各省零售商的要求。村里绝大多数的房子都在那几年里被翻盖,也是目前为止最后一次翻盖。
实际上,户撒刀已经陷入了一个悖论:它因为“锋利”而出名、而畅销、而繁荣,又因为“锋利”而衰落;要想重振户撒刀威风,必须仰仗于它“锋利、耐磨”的传统优势,但这又正是市场对它说“不”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具有自净功能的综合系统,市场不会管户撒刀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它只承认这种现在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这样一种结论的出现,可能不会是我们的杞人之忧:户撒刀将继续它的衰落,直到消亡,它没有翻盘的机会。
四川、浙江等地出产的刀具,其装饰功能大大超过实用功能,它们横扫刀具市场,是理性时代的胜利,也正是户撒刀悲剧所在。有悠久的历史和娴熟的技术作保证,在相关的硬件设施得到改善以后,也许户撒乡还会生产出更适应市场的刀具,但那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户撒刀”了。










